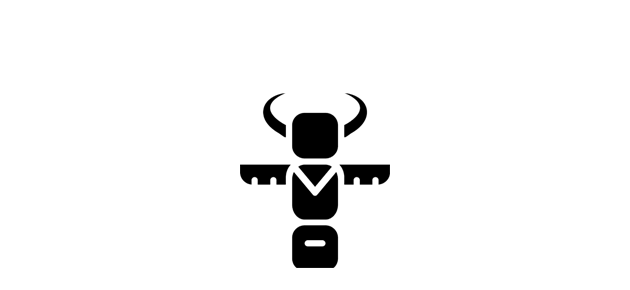上个月底读完了小沃尔特·M·米勒的《莱博维茨的赞歌》。
这部作品出版于1959年,是为冷战危机冲突升级的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自战后不久展开意识形态政治对抗,进而发展出核军备竞赛,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怖平衡相互制约。
小说中的世界可没有这么幸运——热核战争在短短不到20个世纪的时间内将地球文明摧毁了两次。
这部充满了宗教色彩和哲学意味的科幻文学就像是一个晦涩、生动、发人深省的矛盾综合体,因而在震撼之余想写些什么的时候却又无从下笔。在各种亚文化作品中,我们想象过核弹毁灭世界的场景,似乎这已经仅仅是一个制造戏剧冲突与独特场景的题材。如若这般,『后启示录』的《莱博维茨的赞歌》究竟以什么让人觉得难以释怀?
直到近几天前在某档播客上听到了一期由陈嘉映和周濂两位哲学学者以『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为主题的沙龙漫谈节目……
在对话中,两位学者都认同科学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中主流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唯)科学主义的摒弃。
陈嘉映以近代科学以自然哲学家伽利略、牛顿等人研究『第一性质』的发端史为引,提出科学本就是研究事物客观性质的学问,而即便是这些自然科学家也承认,『第一性质』并不是人类追求的全部;科学在解释某些非『第一性质』的领域,只是在解释『How』,而非真正通往解释『Why』的正途。
周濂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人文与科学两大文化领域能否合流,形成所谓的『第三种文化』。这一概念来自于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1959年提出的『两种文化』的思考,以及后来美国作家约翰·布罗克曼于1995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从此延展出的一系列讨论试图为两种文化找到一种达成和解的新领域。在沙龙上,陈嘉映表示不认为存在『第三种文化』,但没有展开来细聊。
……
将科幻文学视为通往『第三种文化』的通道显然是肤浅的。科幻小说属文学的范畴,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与严肃文学距离几许尚存争议,跟严谨的科学更是不在一个维度上。但是,在普罗大众的角度上,科幻文学却也一定程度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让更多人有机会有兴趣去了解更多关于科学原理的知识。
在我短浅得有限的想象距离中,科学的飞速发展固然一日千里,却也无法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是还差得远)。科学为人类贡献出了核弹这样的大杀器——尽管我们不能把谋杀罪怪罪到凶器的身上;而在古巴导弹危机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是人类打从心底里的恐惧让『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怖平衡』发挥机制,使得约翰·肯尼迪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能在相对理智的状态下保持克制,最终达成协商一致,才没有造成如《莱博维茨的赞歌》中描绘的世界末日场面。
插一句,人类还要感谢苏联B-59狐步级潜艇的大副,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尔希波夫。
科学的真理不以人的存在而存在。人文则全然不是如此。
《莱博维茨的赞歌》第二章节中写到的学者塔德奥就带着一些科学主义的气质。但他并非没有人文的内里——只要是人,多少总会怀有些的人文情怀。正是塔德奥这样的科学学者让社会得以在文明濒临灭绝的边缘还有机会卷土重来。
作品中最能代表作者主旨心意的,应该是贯穿了三个章节的莱博维茨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弗朗西斯修士、保罗与泽奇两位院长。正如他们所代表的天主教会——宗教之于人的历史社会,占据了人类心灵相当一部分时空间。对于在二战时期遭受了严重心灵创伤的米勒而言,宗教信仰成为了他日后找寻创伤压力出口的一扇门。而以小说的方式虚构(预言)一个后启示录的世界,正传递了米勒对于前途未卜的人类世界的悲悯。
是人文的共鸣,让我们将科学的震撼以及科学那些数字之外的神秘力量转化为更可感知的情绪。哲学、宗教、文学,莫不如此。
我们是否需要科学?显然地,我们崇尚科学的精神,依赖科学的力量。
那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的悲悯?我只知道,仅仅想像一个没有人文情怀的世界,便会使得我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