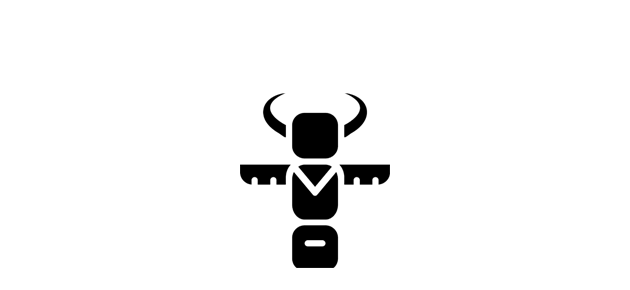听苏阳的《贤良》。起初是奔着听点『花儿』去的,然后就搜到了苏阳。
似乎苏阳这人也说过:『我唱不了传统的「花儿」。我是一个唱不好民歌的人。』然而,毕竟我还是有幸藉此听到了苏阳和他的《贤良》。
西北官话伴随着传统乐器,有一种黄土与黄沙的古朴与苍茫,也时而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朴实无华,而骨子里却有着独到的摇滚范儿。接触过的同类型音乐不多,有些让我想起几年前在某原创音乐节目中听过(同为宁夏人的)赵牧阳创作的《侠客行》,通透且豪迈,大漠孤烟直的胸怀。
再想了一遍,我对《贤良》的认识差不多也就停留在此了——停留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总结之上。
当一个人想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其实也就是在以一种局外人的异域眼光来思考问题。当我试图去思考西北的曲艺这一概念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刷刷地跳出『秦腔』、『信天游』这样一些字眼,继而便是『黄土高原』、『窑洞』、『戈壁』等等意象……这无疑是一种标签化的认知,或许人类就是以这样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来掩盖自己的一无所知。
标签化的理解看似能够快速地还原事物的相貌,却也更多地在用一种断章取义式的方法进行看待,继而放弃对认识事物全貌的努力。
联系到最近在读的一本书也是如此。关于18世纪伊朗君主纳迪尔沙的《波斯之剑》,对我而言,这里头包含了错误的时间(近代)、错误的地点(西亚)——基本是在从前兴趣之外的陌生领域,于是一直都在以某种猎奇的心态在阅读。
『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我在看到插图里的人儿穿着传统波斯服装时这样想到。仿若我有资格以某种姿态来睥睨这些来自异域的东西。
一拍脑门。其实,我只不过是个端着书本本的——借用苏阳的词儿来说——地上的拉拉缨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