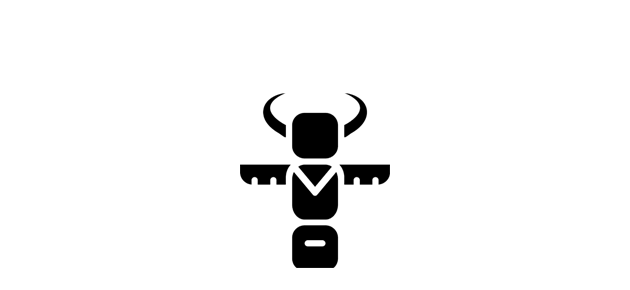呼愁
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城布满了浓浓的“呼愁”。20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给整个国家、国民以及这座曾经是世界中心的城市带来的(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的)颓败感,打小就在他——家道中落的土耳其中产家庭男孩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继而,注定(如果世上有注定)将成为背负着若干沉重历史观的年轻画家——而后是作家的帕慕克——所继承的故乡血管深处的淡淡忧伤,并由他们将这种贯穿了他成长,难以磨灭而去的忧伤唤作“呼愁”。
不管是想象“另一个奥尔罕”,还是欣赏阅读某几个特定领域孤寂艺术家的作品和生平,或是行走在贫民窟和断壁残垣的街巷中,从贝尤鲁到加拉塔,从伊斯坦布尔横亘在两片大陆之上的广阔幅员,到人心内更广褒的内心世界,帕慕克目睹了一个落后民族渴望西化却一时处处尽显蹩脚的丑态,自己也挣扎在家境人情的困惑中。
数船只
作者一度痴迷于在住处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一举世的航海要道,只将异趣寄予观望和计数水面上通过的船只。
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的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
在白昼乃至黑夜,静处城市一隅,悄然观察着某处别致却不见得能招致众人观望的平常风景。
有那么一段小小的时日,我也曾在傍晚时分躲在杭州运河边的林荫下,细细看着每一艘经过此段河道的运输船缓缓驶过。从那锈迹斑斑的船身上最终得知它是来自湖州?泰州?盐城?或是更远的济宁。
京杭运河上徐徐驶过的货船想来无法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万吨巨轮同日而语,但其间的相似性却无法令我不去浮想联翩。日复一日的船只过客如同这座沧桑城市中小小的浮光掠影,最终又有几多人关心这漫漫水道间一闪即逝的蝼蚁呢?
那些艺术家
奥尔罕·帕慕克打小在绘画领域便有不俗的天赋,也许也曾对那终将成为抗击家长意志和人生命运借口和工具的建筑学有着一定的独到理解,众所周知的是他成为了一位知名的作家,这样看来他自己就是一位艺术家。这位知名的艺术家所仰慕和着墨甚多的艺术家,却不见得有多么知名。记事录作者希萨尔、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记者历史学家科丘,这些在身体和内心都烙下伊斯坦布尔印记的本土艺术家了解这座城市太多,都曾以各自分明的个性和创作动力,格格不入地生活在那个在帕慕克看来格外扭曲的时代里,在他们的作品中孤独地散发出浓浓的“呼愁”。
画家梅林倒是纯粹了许多,帕慕克欣赏他的画,崇尚他的画风,在他的作品中“了解这座城市的辉煌岁月”,同时想必他也是帕慕克绘画的启蒙者。
至于提及的诸多自西方而来的有着艺术家身份的旅行者,帕慕克与大多数土耳其人一样,十分关注他们对于这个国家与城市的看法——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对于这些人和他们的看法,他也自信地有着自己理性的见解,如同他曾经尝试着以外人的眼光来睥睨故土,再回过身来以自己的身份去看待它。
最后还是去了瑞士的初恋
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帕慕克的青少年时期(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很难说是完美的,不单单是因为太浓郁的“呼愁”伴随了许多时光(更不是指像家道中落这样庸俗的原因)。填补上青春期对周遭的藐视、学业的无聊、淡淡的惆怅和独自绘画的寂寥的事情,是同“黑玫瑰”的爱情。年轻的女学生,既是他油画中的模特,也是共同游历城市的伴侣,接吻、做爱,美好的人儿,美好的事物。
爱恋本就是一项极尽单纯的事物,“黑玫瑰”就是画里和画外有着单纯美好心灵的寄托,令同样年轻的作者忘却尘世的喧嚣和烦闷,不经意间或已变成专心于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砥柱。
因此,当这位初恋说出她的父亲有欲令她去瑞士上学的计划,其实这已成势必,因为“呼愁”以及成年的现状终将把他——奥尔罕·帕慕克——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就像最后一个章节《与母亲的对话》中写的那样,真实而惨淡。当两人分离的时间悄然到来,即便曾有过做几分抵抗的打算,也只是静静地结束了,没有挣扎,便归于沉寂。
关于奥尔罕
除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没有读过奥尔罕·帕慕克的其他作品。据说此人的新作(小说《我意识里的怪癖》)比前几部作品更多地在描写,或者在暗讽土耳其社会现状和传统矛盾,因此被土政府实施了关照,俨然在故土被疏远。虽未曾读过这新作,唯独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中透露出来的“呼愁”,可管中窥豹感受出来几分。
诚然,帕慕克是一个“故乡忧郁的灵魂”,在讲述自己和别人的故事时,他站在那座忧郁的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