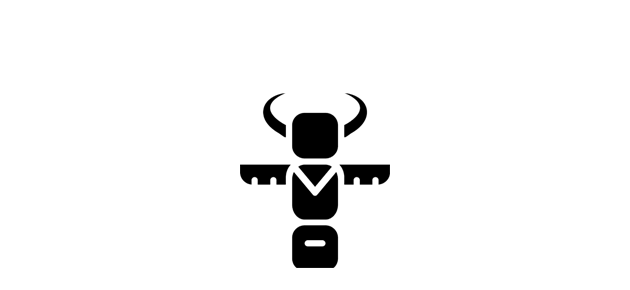寂寞的异乡、孤独的夜晚,大概特别适合思念童年时候的故乡。
1940年,萧红在香港写完《呼兰河传》。这时候,28岁的她,早就已是个只能在记忆里才能拥有愉悦和宁静生活的人了。
在离开小小的县城后,自北向南,长路漫漫而波折;从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到汉口、西安、重庆、香港。她参加过学运,经历过抗战,拿起笔写下了不少文字,也在情感世界里浮浮沉沉。
恐怕,童年和家乡的琐碎——在这时候——才是她真正念及的远方。
呼兰河缓缓流过的小城,彩色的往昔时光:马拉的车子陷进积水的泥坑子里,庙会时节走失的小孩哇哇地哭,小偏房里赶车人家花钱给团圆媳妇跳大神,院子中有二伯与老厨子吵得不可开交。这些都是远在十余年后千里之外的萧红回忆里清晰,具象,还略有些俏皮的画面和片段。
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里,有零星的镜头能瞥见童年时住在东北老宅子里孩提时代的萧红,还有她最亲密,最思念的外祖父的身影。但就像这部电影一样,世人感慨的是她纷纷扰扰的一生,而她自己最挂念的,却是往日里任由她玩闹闯荡的外祖父与他故居那套呼兰河的宅子。
年初的时候曾去往过冬日里的白山黑水,带着《呼兰河传》在入睡前翻看。夜里睡时便是取暖,白天玩乐也是挨冻。那里那样的乡郊、田野,结冻的河流,曾经的小城——我能想象这样的景象值得在某种回忆里带着一些悲伤的情绪去思念。
在乱世中格外熙熙攘攘的都市里,想必无法再次重温和体会。
萧红死的时候还不满31岁,叫人唏嘘。与其同年(甚至还是晚一个月)诞生的同为文人的杨绛,一直长寿地生活到上个月,这更叫人唏嘘。唏嘘了便唏嘘了,但人生的意义或许本就并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依靠那些视角和经历获取了如何异彩纷呈的旅程。
写完《呼兰河传》不到两年,萧红便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在另一个地方,她应该不必再用回忆来唤醒愉悦美好的童年和故乡。
而她笔下的那个地方,依旧飘着袅袅的炊烟,火烧云映照下河流的南岸,摇曳着一大片的柳条。院子里蒿草丛上飞着许多蜻蜓,它们专为红蓼花而来……
有时候呢,不要执着于远方,想一想,你曾拥有过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