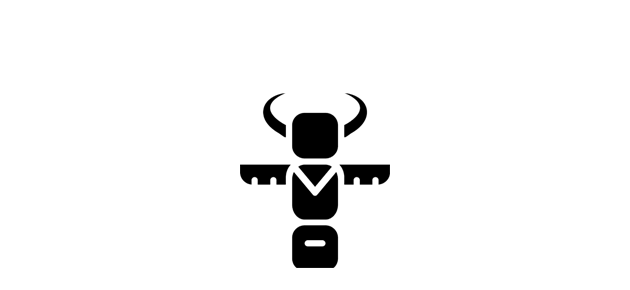说起“黔”一字,最快在脑海中搜索到的印象想必是柳宗元的《黔之驴》一文了。可叹寓言中的驴子稀里糊涂,死得凄惨,最终还落下一个成语“黔驴技穷”,形容拙劣无能,外强中干,并非什么好词。
有人考究,柳河东所处唐代的黔中道管辖了现今川渝湘桂多地,而正经属于今日贵州的土地反而不多;该道的治所黔州其实位于今天重庆彭水一带。估计考究者是不想在某种语境里使贵州省与有着可悲命运的驴子绑定。但无论如何,今天的“黔”字已基本同贵州省完全绑定了。
后世多朝,山高路远的贵州都属于与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边鄙之地。元明清几百年来,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是此地的主旋律。当你所坐的汽车、火车行驶在这穿梭于连绵不绝的大桥和隧道之间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之上时,也就不会对古时于此交通阻塞不便、管辖鞭长莫及而感到半点疑惑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这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在豪掷千金后建设过分完善,反而使人有点猜忌其必要性了。
除此之外,诸如运营了iCloud中国大陆业务等数据项目的“云上贵州”、黔南深山里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先进工程或许也在慢慢改造着当代贵州在世人眼中的面貌形象。
但总的来说,这里仍是一个发展机遇相对较少的西部省份。
云贵高原的崎岖即便在大城市贵阳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时不时起伏的城市路段以及目之所及建于山腰之上的建筑,都与山城重庆很有几分相似;而其中一些老旧低矮,分明建设于上世纪且久未经修缮的房屋,则让我这个初来乍到之人立马联想起毕赣《路边野餐》中的场景。
在见识过“地无三里平”之后的不久,很快便领教了“天无三日晴”。在贵阳的第一个整天,上午分明是艳阳高照,下午忽然风起云涌,突降大雨。也不知道是因强烈对流还是受远方台风影响,总之雨下得毫无商量。后面几日亦频频如此。
这里的食物普遍以酸、辣为特色,形成的原因我不敢妄加猜测。香是挺香的,不过即便是我引以为傲的肠胃消化系统也很快就沦陷了——到达贵州的第三天早上,我开始轻微蹿稀。食物辅料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折耳根(也有当主料吃的例子),偶尔加一点儿颇增风味,来多了确实受不了;水果的典型地域代表则是刺梨,街头小贩捏成果汁,饮一口,绵长的微涩回味无穷。
此趟没怎么和人交流,除了几位网约车司机。既有十分健谈,全程逮着你聊的,也有相对内敛些的,但平均水平而言还是属于能侃。人们操着西南官话,即便口音重些,也不算难懂,随性而富有生活气息的语音语调跟贵阳城里整条街的排挡在深更半夜依旧喧嚣的生活作风在风格上可谓十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