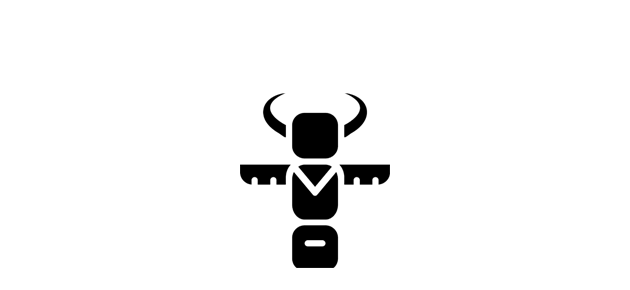在我所有的印象中,奶奶是一个勤劳、朴实、和善、乐观的女性。
大概四,五年前,奶奶还是那个背上锄头就去房前屋后土地上劳作的老太太。耕地、下种、浇水、除草……九十多岁的矮小身躯每天仿若有用不完的力气。
后来,慢慢地,这些城市角落处的荒地都被盖了房子、做了绿化,奶奶种点什么的爱好也就渐渐被剥夺了。但她也是空不下来的。住在我家时,也老想着有哪些家务可做。即便手里闲下了,心里总在惦念些什么。
奶奶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她的上半辈子是贫穷的。因而节俭和勤恳一样,都是她最倚重的美德,也是她最显著的生活特点。然而到了我们小辈这,她又变成最大方的人,总是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我们回家的时候。
中学时有挺长一段时间,寒暑假或周末都去奶奶家吃中、晚饭。叫开门之后,八十岁上下的奶奶回到厨房里烧菜,我兄弟俩则在客厅里跑跳玩耍、看电视。
奶奶从未嫌麻烦,且以此为乐。我可以从她的言语中和眼里看出来。
奶奶从前炒的金瓜粉干,喷香,配白粥喝。聚会时,她最拿手的菜是砂锅炖的五香鸡,格外下饭。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想着变点花样——包包子,蒸金团,烤肉麦饼……“喜欢吃的话,下次再做一次。”她总会这么说。
这段时间里,随着年纪增大,奶奶听力衰退。在厨房里时常听不见敲门声。于是我们从增大拍门的力度,到往房里打电话,再到跑下楼到厨房窗户下呼唤……但凡奶奶听到了,就会一边说着“来咯,来咯”,一边迈着她的小碎步走过来,笑盈盈地开了门。
对我们而言,奶奶从来都是那个充满耐心,极少苛责的人。
正因为奶奶和蔼可亲,自年幼时起,奶奶家就是一处令人心安的庇护所。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夜晚我兄弟俩在家,玩腻后等待父母未归,觉得心焦,便从小城的城南走到城北,来到那时候奶奶住的家,喊奶奶开门呀。叩开门,奶奶唤着我们的乳名,略带些惊讶地接我们进去,我们的心也就踏实了。
在奶奶心中,身边所有人都是良善的。她乐于与人交流,并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人。
奶奶最喜家人团圆,坐在一张大桌前吃饭。逢年过节,若子女儿孙能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她必然是喜笑颜开,最是知足。
到了离别时,她是那个即便已到耄耋之年也要起身送你到门口、楼道口、单元口、楼下车门前,摆着手嘱咐你一定要路上小心、保重身体的那个人。
奶奶总说,生活很好,对现下的所有都很满意了。
奶奶的身份证上印着她的出生年份是1928年。民政局搞错了,她属兔,过了新年原到了她的本命年。
如今,奶奶离开我们去往那处至善之地。整理完她的房间,觉得不舍。思忖不得,只想跟小时候与她作别时那样,对她说一句:奶奶,拜拜。